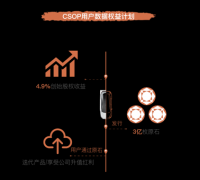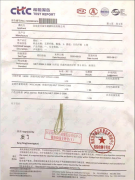杭州10月19日电(柴燕菲 王逸飞)GDP由1949年的15亿元增长至超5.6万亿元,居中国第四位;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和34年全国居首……在地方发展跑道上,浙江是公认的“种子选手”。
“大省”“强省”标签背后是发展历程的筚路蓝缕: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海防前哨之地的一穷二白,到实现温饱、小康和全面小康;从计划到市场,再到民营经济崛起;从一次次突破旧体制藩篱,到全面深化改革瞄准高质量发展……没有先天优势的浙江,用持续“突围”赢得了先发优势。
这其中,建立起调动和激发千百万人积极性、创造力的体制机制是核心一环。其改变了浙江发展面貌、建立着发展优势、塑造起发展环境,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无数生动、丰富故事中独特的发展样本。
 浙江的“网红”乡村——东梓关村。 富宣 供图
浙江的“网红”乡村——东梓关村。 富宣 供图
富民强省:绝对贫困转身全面小康
浙江临安,开网店卖山核桃的白牛村村民已为“双十一”忙活了。该村原是当地最穷村庄之一,现有淘宝店68家,去年人均收入3.35万元。
在浙江,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116元和47元,增至5.56万元和2.73万元。包括该变化在内,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成为浙江的历史性转变。
千方百计促民富,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——以此为出发点,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浙江的重要方法论。
新中国成立后,该省在全国第一个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——实现包产到户。1966年成为首个超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亩产指标省份。工业上浙江推进公私合营,实行手工业合作化,兴办全国最早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。
伴随着改革开放,浙江加大体制机制创新步伐。
至20世纪80年代,农业结构长期是“粮经特”——先保证粮食生产,再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。为让农民富起来,浙江提出按比较优势原则调整农业结构为“特经粮”,由此其农业走上商品化路子。
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,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,让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劳动力,浙江的方向也是后来“三农”改革的方向。
包括推进农村工业化、大力发展专业商品市场、率先停征农业税在内,几十年中,体制机制优势让浙江实现了率先发展。21世纪初,该省GDP超6000亿元,跃升中国第一梯队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9279元和4254元。
为推动新一轮发展,2003年浙江提出“八八战略”,开宗明义强调“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”。以其为指引,不断缩小贫富、城乡、区域差距,成为该省富民强省实践的重要特征。
推动区域协调发展,浙江启动山海协作工程。以山区县庆元为例,协作地长兴县每年资助50万元帮助其改善办学条件。2019年长兴已拨付帮扶资金173万元,总计538万元。
缩小城乡差距,该省启动“千万工程”、县域医共体建设等,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涌流、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。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农民收入破1万元、2万元的省,全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,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省。
民营经济:从不得不然到深以为然
主动向体制机制要优势,浙江亦在“起家”过程中建立起自身发展特色。民营经济的成长即是体现。包容、倒逼、服务等关键词,串联起了浙江这一故事。
1980年,浙江颁出改革开放后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;1982年,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……回顾浙江民营经济的发轫,体制机制优势最初以包容态度这一外在形态表现出来。
这种包容,是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喊出的“出了问题我负责,哪怕丢掉乌纱帽”;是温州民营经济因“八大王”事件噤若寒蝉时,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“重点户专业户”千人大会上亲自为个体户颁奖。
后伴随民间经济创新的活跃,浙江有形的体制机制开始发挥更大作用。
1992年,浙江一方面给原来挂靠集体戴“红帽子”的企业帽正名,同时推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,推动非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占到经济总量的50%以上。
新世纪初,面对要素短缺、环境承载力制约等“成长烦恼”的浙江,在“八八战略”指引下提出“凤凰涅槃、腾笼换鸟”。“淘汰落后产能”“三改一拆”“五水共治”等在十余年里先后施行,浙江民营经济因倒逼焕发新质地。
“我们引进废水重复利用技术和先进生产线,因降低了耗水量和人工成本,总成本反而降低了。”金利纸业负责人胡永明说。其所在的杭州富阳,此前提出的三年时间淘汰全部670万吨造纸落后产能目标已近完成。取而代之的是高端装备制造、数字产业等。
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,到近年持续下行的外部经济环境,经历倒逼的浙江民营经济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,增加值从十多年前不足万亿增长至超3.5万亿。
愈发严峻的经济形势下,浙江以体制机制服务民企的力度也不断加码。
去年,该省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1条意见,把市场准入、融资难、融资贵等问题通过政策方式支持解决。浙江11市也制定叠加政策。今年,浙江部署开展服务基层、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的“三服务”活动,其中服务民企成为重点之一。
2018年,民营经济已占据浙江GDP的65%,税收的74%,出口的77%。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说:“浙江民营经济经历了从不得不然到自然而然再到深以为然的发展。其中可深深感受到群众与基层的创造性活力之伟大,及政府长期不懈努力之艰辛。”
 浙江某企业车间。 张煜欢 摄
浙江某企业车间。 张煜欢 摄
环境再造:效能革命催发内生动力
内部活力不断激发,关键还有一次次冲破旧体制机制,再造更符实际的现实环境。
改革开放后,浙江打造的宽松环境塑造了个私经济发展、温州模式、义乌小商品市场等。关于浙江的“大市场小政府”“无为而治”等评价也由此而来,在侧面体现着该省的独特“智慧”。
无为与有为从不能绝对定义。长期以来,浙江政府“不恋权”——向市场放,也向基层放,义乌是一个缩影。
本世纪初,快速发展的义乌遇到了种种体制机制瓶颈。如国有银行在义乌只能设县级支行,授信权限低导致融资难;企业进出口备案登记、减免税等要跑到金华海关办理……
“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”。2006年,浙江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。除规划管理、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,赋予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,金华市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。义乌一时被称为“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”。GDP从2005年的300亿元增至如今的1200余亿元。
 浙江某地行政服务中心。 张茵 摄
浙江某地行政服务中心。 张茵 摄
浙江同样把体制机制效能革命延伸至政府内部。
三年前启动的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,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技术支撑,通过改革体制机制、流程再造倒逼政府自身改革,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。目前浙江已实现省市县三级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100%全覆盖,满意率96.5%。
“‘最多跑一次’改革最大特点是简洁明了,提法之易懂、目标之清晰、要求之高是多轮审改所未曾有过的。”卓勇良表示,其体现了浙江提高政府治理水平、政府效能,减轻地方、机构和个人负担的决心,在源头上提升了经济社会运行效率。
当下,此改革一方面在浙江不断扩大外延,延伸至公共服务领域。如医疗领域,费用结算医后付、刷脸就医已稳步推进。另一方面,以其为牵引,一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亦在浙江展开。工业领域推出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,项目领域推出“标准地”改革……
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公开表示,“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、瞄准顽症痼疾、找准主攻方向,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突破、纵深推进,努力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。”(完)
凡注有"财经世评网"的稿件,均为财经世评网独家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;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"财经世评网,并保留"财经世评网"的电头。